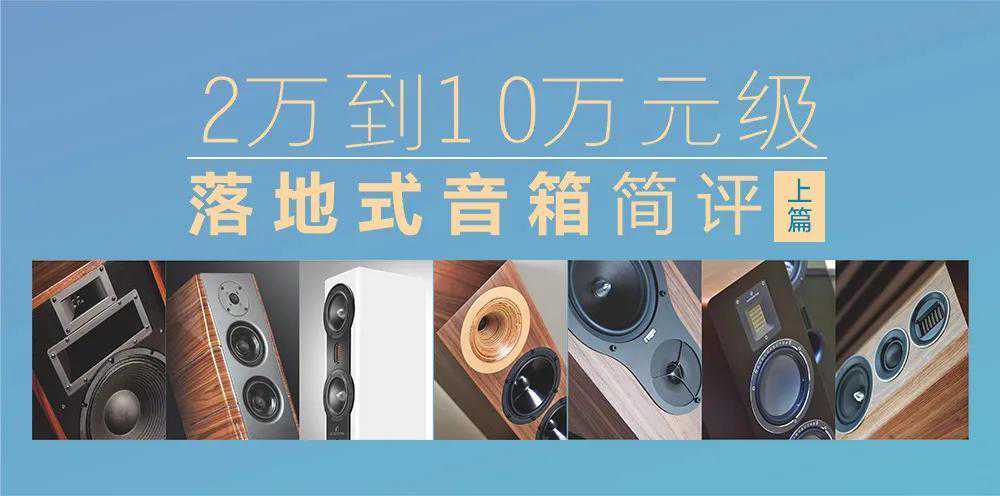文/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G1604王硕
(序)
那天我们登上山来到湖边,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环绕着湖的片片山坡叠青泄翠,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冰僵的天穹。凝眸望去,长空寥廓,但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抚过蜿蜒起伏的芒草,微微拂动我的头发,旋即向身后的杂木林吹去。树梢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一)
即使在度过不止多少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原的风。可是关于大湖,却是像是只在梦中见过似的,为什么会忘掉它呢?它就像是象征着某种美好的记忆,无可避免地从我的躯壳里流走了。想要回想起的时候,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地仿佛可以用手描摹下来。
离开那面湖,我们回到高速公路边。看着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长河,我却有些畏缩连,浑然忘了自己来时是如何轻快地跑过车道。“跟着我。”那时还年幼的表哥对着年幼的我说,他瞪大的眼晴像是大湖的湖面,在阳光下折射出好看的琥珀色,瑰丽的光芒让我不由地信服他。抓住一个车流的空隙,他蓦然拉住我跑向对对面,同行的两三个孩子也嬉笑着跑过车道。强忍着刺激的心情,我打量着周身的一切:小小的我们刚淌过水赤裸着上身,身子像才出淤泥的藕瓣,犹有未被河水洗尽的垢物抹匀在皮肤上,照射出粼粼的乌光。“那是水库,太深不能下去的。”记忆中的表哥这样说。这才让我想起来,我们原来要找个地方再洗个凉爽的夏日澡的,可大家都因为大湖让人置身于梦境的景色失语了,竟然没人敢提出玷污大湖倒映出的明净天空。至今为止我都无法确定那面湖真的存在过,就像泪水洗过的澄澈的世界,入口已经永远对我关闭。
(二)
表哥可能永远不会变知道,他熟已为常的风景,早已珍贵到让我在梦中希冀。盛夏的清晨,他常载着我从南向北到镇上的集市去,为舔几口解渴的冰棒,为串一绳绿油油的蚱蜢。与车辆滑过静默无声的高速桥遥遥相对的,是镇子另一头长长的绕山铁路。火车隆隆的轨声总会寥若地打破小镇晨间的安静,随后又散入一片濛濛地晨雾中,只能依稀传入我的耳中。尚是青绿的油菜田伴着贯通镇子的乡路延展开来,不远处还有两边都是水泊的窄窄田道,再远初是依山而建的村庄。初升的朝阳带着金辉打碎浅浅的树影,温暖而不炙热。
那时的表哥还未沉默寡言。遇到路边去干活的乡亲还会减缓速度聊上几句,那人多半还会看着我说:“城里来的孩子啊!”随后扛着农具慢悠悠地走开。小镇就在不远处了,带着它与深邃的幽谷相连的清静悠闲迎接着表哥和我,如果不是赶集的日子,镇上的铺面大多都是冷清的,有些人既要等到近午。这时夏天的散漫和灼热才惊醒着扑面而来。
那时的我还算温顺羞涩,表哥转进了颠簸的小路,我急忙紧张的抓住他的肩膀,澎湃的新绿和青黄簇拥着我太多新鲜的食物,让我目不暇接.山麓终于褪去之前青涩的模样,露出诱人的弧度。大地是那么苍翠的展开,直到有些炊烟的远方。每一方池塘都亮丽得如同梦里的笑容,每一条小路都清秀得像一句诗歌,泉声、鸟声、蝉声,花影、云痕、水涡,光和影被稀稀疏疏的树叶混剪出好看的形状,他们都祝福着满心欢喜的我。
(三)
那个地方是不懈努力,为何当时全然没有发现?
很漂亮。很漂亮。
原来我也曾那样被祝福过,只不过那时的我全然没有发现。
早晨,还没睡醒的城市有点脏。大梦初醒,我没来得及回味,匆匆洗漱,往口里塞下早饭,出门补习。厚重的雨云下是一整片暗淡的风景,路上已经积蓄许多坑洼,除了踏碎枯枝败叶和溅起腐烂果泥的脚步声,雨水敲打在树叶上摇摆婆娑,覆盖住落在水面的声音。褪色的社区宣传海报已经年迈得不知道属于哪个年代,喘息着将我引导向狭窄逼促的教室。来得将上午的试卷和中餐一起消化,我不得不忍受施工地和的嘈杂尖锐的叫喊声,在被窝里迷迷糊糊也不上一个钟头的午觉.蓬头垢面地爬下床,来不及整理就急跑下楼,和惨烈的天色入一起迎接我的,许占满整个下午到晚间的课程。拐进巷子里,生硬粗大的电线,和沾满灰尘的树叶遮住天空,勉强刷上一部分新漆也掩饰不了旧败的楼面,以及破烂的墙皮,共同诠释着小巷的狭窄和昏沉。而这样拥挤的巷道,在学校附近不知还有多少,共同联绘起一副衰老的老城包围住校门,留下零零碎碎大小不一的培训中心的散落各地。
到了傍晚结课,公寓楼和杂居楼歪歪扭扭地倚靠着灯光分外明亮,我汇入鱼贯而出的雨伞,努力穿梭在形形色色的学生中,仅能望到西边的天空,灰色的云间落了深沉的夕阳。穿过老城区人家敞开的门户,倒映着电视节目的餐桌上热气腾腾,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所营造的生活片段不断从视野里略过。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被这种强大的未知性压倒了,雨天的冷气吸入体内,我只能更加焦躁地思考着。无法言明的抑郁和无法申诉的苦楚给每一张路过的疲惫传递,等我回过神来,一天接近尾声,只收获了茫然。而一想到这种痛苦还要持续三年,舌尖的苦涩就要蔓延到全身。
晚饭间,母亲照例说起家乡小城发生的琐事,哪户的长工短工偷了东西,又有哪个游手好闲的亲戚蹲了局子,哪家新成了婚、新娘子自然还是本地人……但我儿时的玩伴,我所熟识的人,他们消息一下子从远方的小城跋山涉水而来,累得只剩下只言片语、波澜不惊。每当我听到这些虽然晦涩却又像镜子的碎片一样锋利的消息,总会想起一条蜿蜒缓缓流过的小溪,蜿蜒汇入大海。可大海是那样平静淡然,我会感觉隐隐不安,就像是海面下所深藏的暗流,将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拖入旋涡、再难逃脱。他们就在小城里经历着我所不知的跌宕起伏,掀起我所不知的波澜——当然也包括表哥。
“他呀,”我偶然问起母亲,她漫不经心地说“不就是原样,好不容易送进五年制的技校,也没认真上过学,逃课、抽烟照旧,今年你姑父拖沙的活干了准备去外地打工,你姑母死命不让,还在城里租了房子,看着你表哥。”母亲踌躇了一会儿,还是接着说下去,“你爸瞒着我借了公园贷款帮你姑父买出租车,让他先跑几年,你表哥要是还没学到什么本事,估计到了进社会的年纪就接着干下去吧。”我失去夹菜的兴致,放下碗筷,默默咀嚼这些话中的信息。
(四)
那年夏天以后,曾在小城里与表哥断断续续照过几次面。他总是比上一次见面时长高一些,也更沉默了一些,儿时他的面孔古城阳光般的无邪与温暖,已经随着逐渐分明的棱角远去。他自在城里上中学以来就渐渐叛逆起来,寄住在亲戚家时而逃课夜不归宿,为此姑母伤透了脑筋,每每让他和我多聊。我费劲心思打开的话题不外乎是打游戏到通宵之类,也尝试过提起所熟悉的电影音乐,但他一概不知,话题逐渐终止,余下尴尬。静下来时,像是默默的细雨隔在我们之间零落,生疏地无话可说。我只能细细研磨过彼此多年来的变化,察觉到他眸子不再有晶莹闪烁的光彩,颜色缓缓的沉淀,变成积载的年轮无力流动。留意起他的发型,剪成了与城市孩子一般无二的西瓜头,下意识拨弄发型的动作也一般无二,说起普通话说的语调一般无二,只是提起的陌生名词,难堪而不适的样子才暴露出深深的自卑。
勉强从密密麻麻的公式中脱身,一定是已经近夜深,沿着大街小巷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在街市上空。艰难地在被窝里舒展麻木的身体,我总感觉关于表哥有什么东西难以释怀,就像是很久以前寄存在他那里一件宝贵的东西,
我想起来了。
那个小镇,我还去过一次。初中毕业落寞而颓丧的夏天一过,我在离开小城前最后一天萌生了无论如何去一趟小镇的想法,可能是早已对将要迎来的沉重日子有了预感,可能在那时就已经猜测到:我与表哥的生活将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改头换面,今后只能在各自的路上愈走愈远。
当我再次站在沿着山涧的青石板上时,表哥迎着夏末的细雨向我走来,他的脸庞瘦削,也看不到儿时的婴儿肥,清爽的衬衫配上牛仔裤,裤管上卷显得双腿修长。我们久久沉默不语,如同全世界的细雨都在全世界的草坪一般的沉默在继续。突然他笑了,瞳光明媚生辉,琥珀色的光泽像是清风拂过草地,使我再次幸福的跟上他,我们路过小时跑跳经过的矮檐翘瓦,老人正在檐下拆下木门,用熟悉的方言和他打招呼;路过通向公路的橘果林,满鼻饱含泥土的芳香,饱沾新橘未熟的青涩味道的空气;最后来到高速公路前,“哪个水库”我笑着对他说,然后一起凝望对面的青山,好像能望见那山的身后,微风吹拂的芳草地和群山环绕的大湖。狗的吠声再次由远而近,从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传来。雨过天晴,我们跟随着阳光下安静的浮尘一齐下山去,有默契的不再提穿过像儿时一样大胆穿过公路的想法。
“要不要骑摩托带你逛逛,像以前一样。”表哥眼里不再有城市带来的缄默和无措,回到小镇的他有孩子似的自然,温暖而不炙热。我也不再是那个胆小又好奇新鲜的孩子,没有多说坐上后座,路经油菜田金黄灿烂,风光无限,比小时后看到的青绿多几分韵致与心动。沿途平地盖房多了很多,有不少地基已经打下待建,再远些有施工的公路,一切都看起来熟悉的同时多了几分变化,就和这时的表哥一样。那天表哥停下来跟我说很多话,我们踏着土壤缓缓前进,夹杂着绣眼鸟清脆的啼鸣。他说高铁以后可能会经过小镇,还会有新路修进小镇来来,说他有女朋友、也曾带她骑摩托兜风,说自己已经学会了姑父的运沙卡车怎么开……黄昏渐至,粘着雾似的小雨再次飘摇起来。我们都清醒了不少,久久不语,想着怎么倾诉几年来的心意。
(五)
焦灼寒冷的空气,时而高昂的嘈杂和风撞上玻璃的震颤,在廉价的出租屋里,我怎么都想不起那天傍晚表哥是什么表情。在夏日即将结束的细雨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遗憾地进入梦乡前,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在祝福着我,那是是表哥,他赶紧做一个慵懒平淡的小镇青年,留下我在陌生城市里忍受日剧增的压抑和肥胖,靠回忆收获平凡的幸福。他会乘上一个长发清隽的女孩,穿过温馨的霏霏细雨,穿过雨后叠青泄翠的山坡,穿过蜿蜒辽阔的田野,向着延伸的前路与风光驶去。那也曾是我想要的模样。关于他的一切都在温柔地祝福着我。
梦中,我们一行人从湖边下山来。找到凉快的溪水冲了凉,粘了泥水的身子像刚出淤泥的藕瓣,粼粼闪光。甩着湿漉漉的头发,我们踏上回家的路。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下雨。
黑夜和雨声温柔的拥裹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