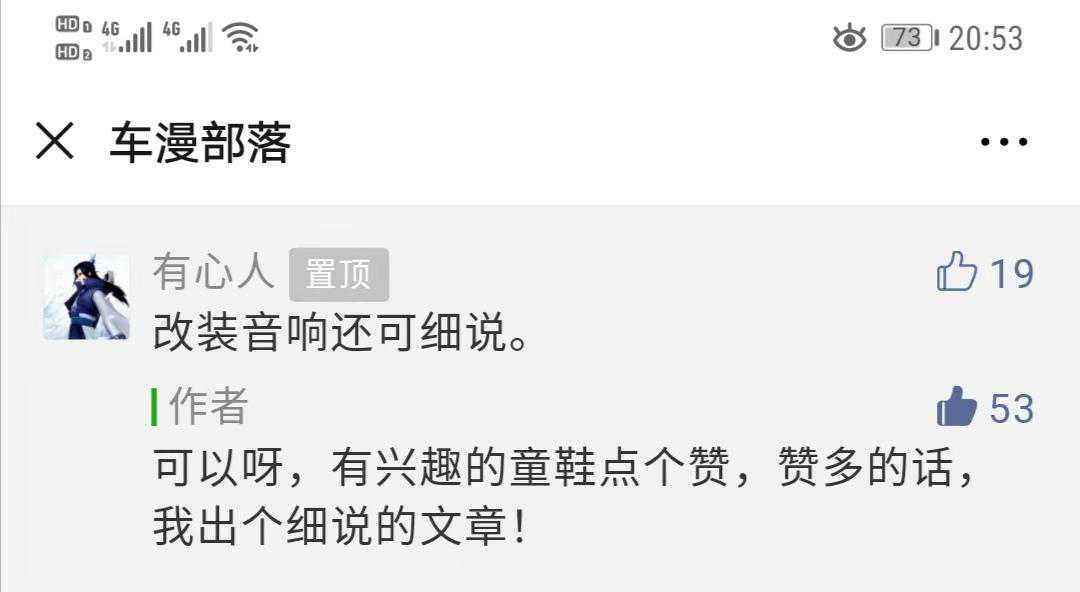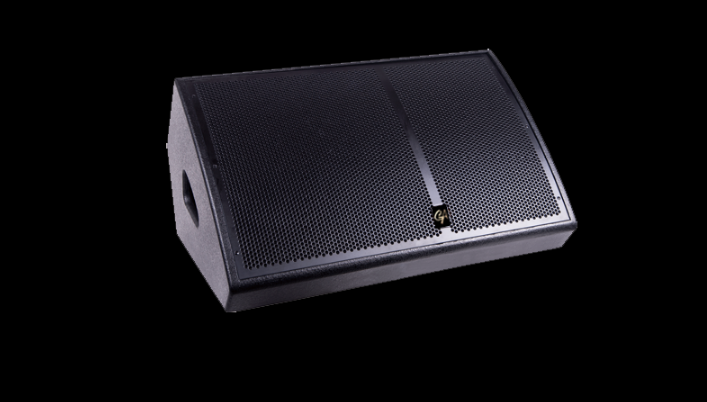那一年,也就是肖家媳妇跳水死的那一年,我刚好出生。这是后来才听人说的。肖家媳妇跳了两次水,第二次才成功。第一次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是在早上大概六点左右,天还只是麻麻亮,刚好是冬天嘛,枯水期,所以她下了水,一直走,走了十多米远,水还只是漫到胸口,恰好这时李老二刚好出来收网嘛,他在码头上一瞧见,赶紧撑排过去,一拽把她拽上竹排。被拽上竹排后,肖家媳妇不哭也不闹,就像座雕塑,只是牙齿敲姜似的得得得地响,鼻子一道道喷着白气。可是过了还不到半个月,肖家媳妇又来了。这回她比上次早了一个小时,天还黑着呢,李老二估计也还在被窝里,所以当天亮人们发现她时,整个人都成冰棍儿了。只是大伙不太明白,水不是很深嘛,并没有漫过人嘛,她怎么就把自己弄死呢?
是呀,肖家媳妇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弄死不可呢,后面再说,先来说说这肖家。这肖家,据说是我们这小镇来得最早的第一户人家,那时我们小镇还是一片荒芜嘛,只有野草和野狗,还有一条河,河岸有几棵大叶榕,这肖家当时不是大财主嘛,用小船从上面的百丈、中平打水路运粮到运江,运江不是在柳江边上嘛,再上大船一直下悟州、广州。当时押船的是肖家三少爷,好几十条船呢,我们小镇不正好是中途嘛,每次总要在这榕树下扎船休息,有次他上岸溜达,左瞧瞧右看看,觉得风水不错嘛,便在这榕树下修了个码头,青石板码头,后来又在码头上搭几间屋子,算是给船工们有个落脚的地方——再后来连他自个儿也住下了。于是,跟后聚的人便越聚越多,有犯事逃难的,躲兵灾的,总而言之,五湖四海,杂七杂八的姓,不多久,便成了一个小集镇。不消说,肖家当时肯定是首富了,除了继续船运外,还在镇上开了染布坊、小酒肆,杂货铺什么的,好不风光。可是这史书上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王侯将相,五世而斩嘛。肖家斩的更早,只有三世,等到肖家三少爷孙子这一代,开始破败了。你想一想,你自个儿认为家大业大,什么也不想干,整日游手好闲,提鸟笼,抽大烟,外加赌,就算金山银山,也要让你败光呀。后来又来了土改,你肖家不是大财主嘛,该收的收,该没的没,所以后来肖家尽管人丁兴旺,分了好几支,和平常人家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嘛。
其实早在土改之前新崛起的还有周家。据说周家是从广东过来,到底带来多少金银财宝谁也说不准,总而言之是开了当铺,高高的炮楼,现在还在嘛。不过现在也不属周家了。风光一时的还有简家。简家来得稍晚,大概祖坟葬得好吧,出了个民兵队长,抄地主财主家时不是瞒了一点金子嘛,所以后来也发了。人发了自然想显摆,所以后来这简队长便打算把自家旧屋拆了,再起堂皇一点,便跟隔壁冯家商量,说是要以飞檐为界。冯家可不干,说,当初俺房子起得早,起得矮,你后来才起,起得高,飞檐飞到俺这边,幸好只飞了一米多,要是飞过来把俺屋子都盖过了,俺这屋子不全归你了,哪有这个道理的。后来闹到土管所,土管所的人来了一瞧,也说哪有这个道理的。简家仍不肯罢休,又请来司法所的人,司法所老张不是和简家关系好嘛,所以简家以为这下准能把冯家拿下,不料老张来了一瞧,半句话也说不得。事情就摆在那,你总不能凭权力和关系睁着眼瞎判吧,群众的眼睛可是贼亮贼亮,要是那样的话,别人咒都要咒死你。所以最终还是以墙为界。简队长咽不下这口气呀,想不到一个小小冯家,竟然拿不下,真是可恶!可恨!所以后来旧屋都还没有拆嘛,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背后被人给咒了的缘故,背上长了个疮,不到三个月,乌呼了。这一家之主一乌呼,自是树倒猢狲散,老婆改了嫁,女儿也嫁得远远的,只剩一个妹子,就是嫁到肖家的肖家媳妇。
肖家媳妇可不像她哥那样横蛮霸道,她贤淑得很,甚至没有跟婆婆拌过半句嘴。可肖家不是没落了嘛,又赶上那么个年代,男人又只一个赌,就算你再贤淑再能干,早出晚归,始终没有办法一个饱字,再加上自己没有生养,这可是天大的罪呀。其实肖家婆婆也不是一个坏人,她只是一个气,偏偏她这气却只撒向媳妇一个,七老八十的人了,从早到晚丧门星、扫帚星的。虽然不是当面骂,可媳妇不是聋子呀,只能悄悄落泪往肚里咽。
活着还有什么盼头,没有盼头呀,又不是恋人闹别扭,也不是什么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哀莫大于心死,再说娘家也回不去了,回去干吗?所以只有一个字——死。肖家媳妇不是跳了两次水嘛,第一次被李老二救了起来,其实你李老二别说救了她一次,就是救两次、三次、再多次,有什么用,没有用!肖家媳妇被人捞上岸,全身都僵直了,只有脸上有两行水,也不清楚是河水还是泪水,这个大概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