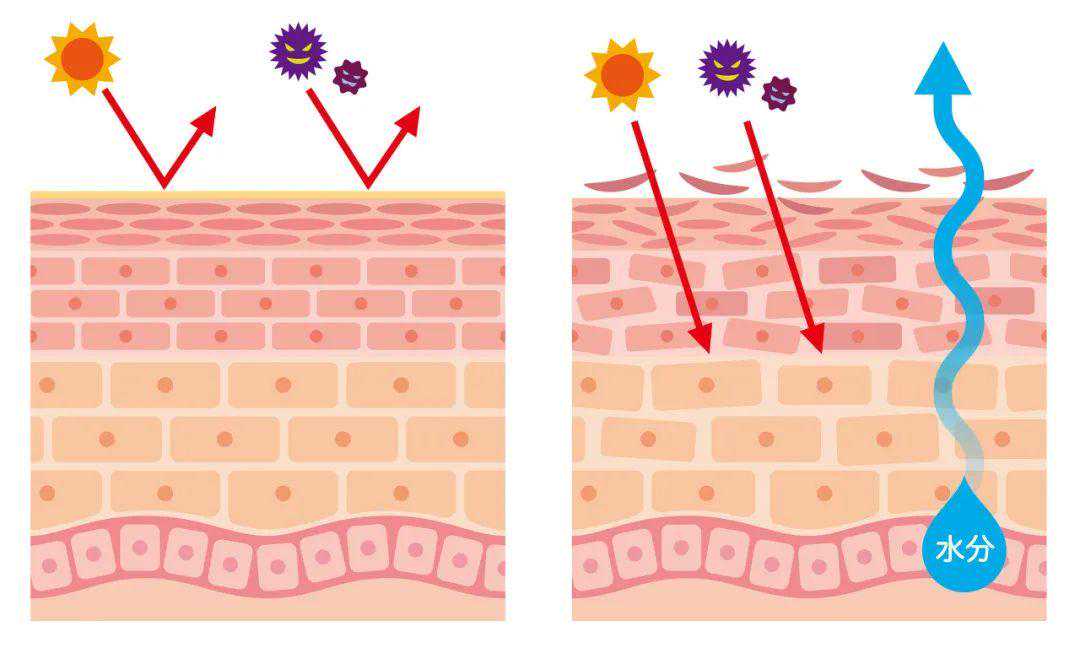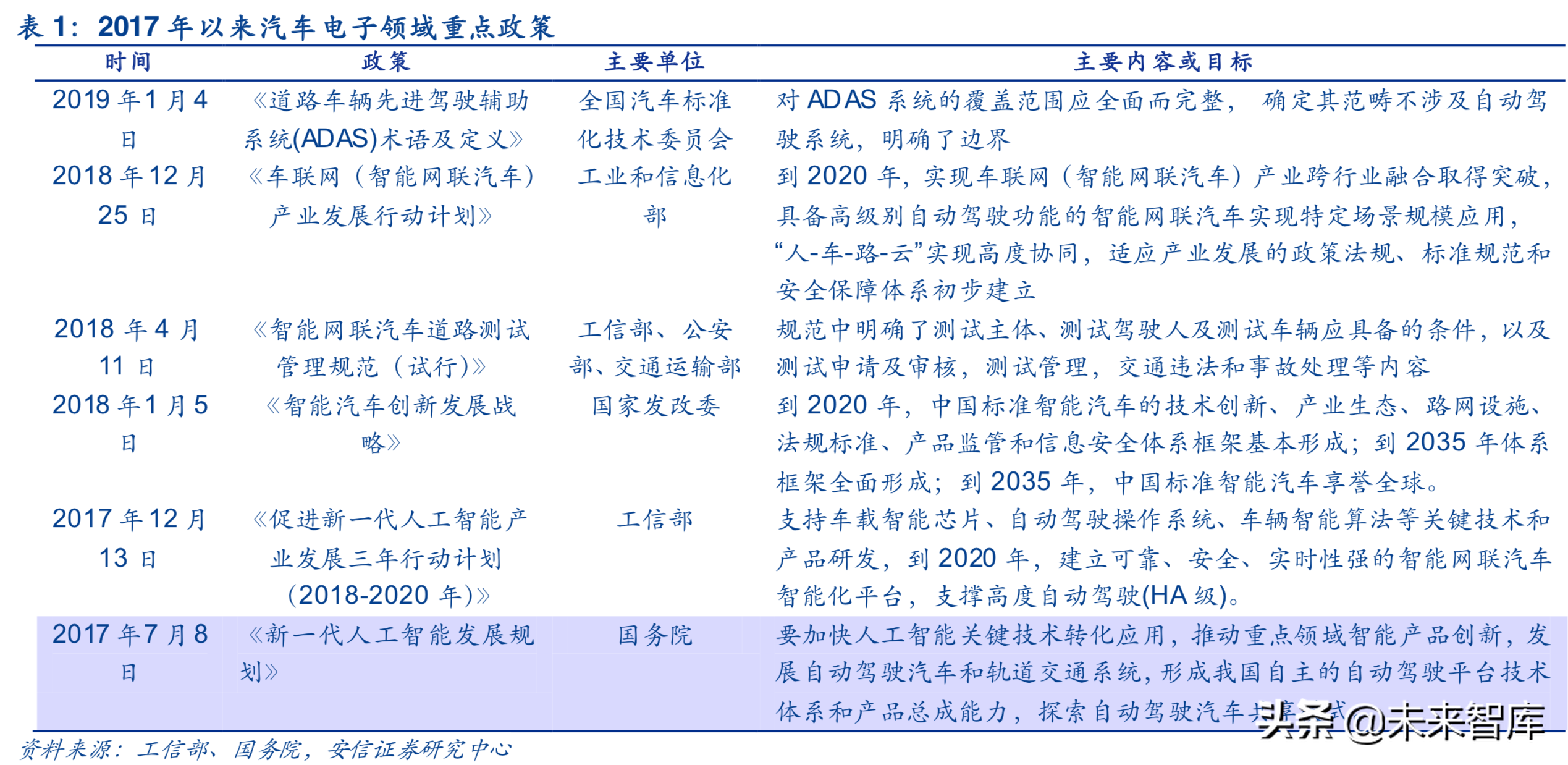倪天伦陈学广
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38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
罗兰·巴尔特
“图像修辞”(Rhétoriquedel'image)概念由罗兰·巴尔特于《图像修辞学》一文中正式提出。该文发表于《交流》(Communications)杂志1964年第4期。巴尔特依据他在同期刊出的《符号学原理》中的“涵指系统”理论,深入分析了意大利“庞扎尼”(Panzani)广告图像的意指原理,后成为图像修辞分析的典范。然而,随着“图像修辞”“图像修辞学”等概念的广泛使用,对“图像修辞”的内涵理解产生了混乱和模糊,甚至出现了争议。“图像修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该概念会产生混乱和引发争议?在巴尔特提出之前,“图像修辞”有无更深的哲学根源?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解开围绕在该概念周围的谜团。
“
一、“图像修辞”的提出及内涵
仅仅知道这些修辞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能指形式是以何种方式发生意指作用。用巴尔特的原话说就是:“意义是如何进入图像之中?意义在何处终结?”巴尔特发现,包括照片在内的图像,都包含两种信息,一种是外延性的,一种是内涵性的,并且这两种信息共同构成图像修辞的“涵指系统”。“涵指系统”理论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文中重点阐发。所谓“涵指系统”,是指存在某种包含直指平面和涵指平面的复合系统,而涵指系统是一个表达面本身由一直指系统构成的意指系统。该理论原本是巴尔特用以解释文学文本系统的意指原理,如果将之运用到图像修辞的分析上,便转化为研究图像“原本信息层”与“象征信息层”之间的关系,即图像“原本信息层”的外延系统成为“象征信息层”内涵系统的能指平面。
然而在《图像修辞学》的文末,巴尔特意识到,单单列举图像内各种类型的内涵指符,抑或是揭示某个具体图像的意指原理,都不足以建立起一门图像修辞学,“这门修辞学只能基于一份相当完备的清单才能建立起来,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份清单中必然会有古典修辞学中已经发现的修辞手段”。而这也为图像修辞分析指明了另一条方向,就是探究图像意指过程中所借助的具体修辞格。于是修辞学家开始套用语言修辞学中语词和句子的修辞方法,以推演图像所使用的修辞技巧。巴尔特在《阿尔桑保罗:修辞学家与魔术师》一文中,以画家阿尔桑保罗的物体组合式肖像画为例,揭示出图像中所使用的隐喻、换喻、讽喻、复词、反命名等大量修辞格,并强调“阿尔桑保罗将绘画变成一种真正的语言”。雅克·迪朗研究一千多幅广告后指出:“广告使用全部的修辞格,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唯独口语才是这样:组合的修辞格(即句子的修辞格)和聚合的修辞格(即词语的修辞格)。”由此可见,巴尔特所提出的“图像修辞”内涵随着图像修辞学的逐步建立进一步发生衍变,在有些语境中还可以指代图像所使用的修辞格。极言之,巴尔特笔下的“图像修辞”既指代图像中具有明确内涵所指的能指形式,又可指图像发生内涵意指所使用的修辞手法。
“
二、“图像修辞”与“图像再现”的混用
米歇尔
然而在西方语境中,与“再现”“相似性”等概念紧密相关的摹仿论是西方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柏拉图认为,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形象,是因为诗人和画家一样,都是通过摹仿真实世界的影像来创作。“影像”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是个重要的概念,多次出现在他的对话中。“所谓影象我指的是阴影,其次是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特别是他的“洞穴”隐喻,揭示出影像与可见世界相似却不真实的特质。洞穴之中的人们被火光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像所欺骗,以为这些影像就是事物的真实模样。也就是说,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摹仿论正是建立在摹仿事物与被摹仿对象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诗与画只是与真实世界相像而已,它们摹仿事物的性质而成为现实的再现。从这个层面来说,语言和图像都是一种摹仿的摹仿,一种相似物的符号再现。于是“形象”一词在柏拉图那里等同于“相似”,等同于“再现”,是一种幻觉主义,一种与理念相对的存在。特别是绘画,柏拉图将之视为自然符号,并与作为习俗符号的语言相区分。绘画与现实事物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为绘画摹仿事物的外形、线条以及色彩,而语言则是“用声音摹仿某事物的人在给他摹仿的事物命名”。总之,艺术依据“相似性”摹仿和再现的思想构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
柏拉图
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将“图像”等同于“再现”的观点极大地混乱了“图像修辞”的含义和使用。进而,“图像修辞”被等价替换为“图像再现的修辞”。而这种“图像再现”极可能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即“图像”本身成为一种修辞格。比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阿喀琉斯盾牌精彩的长篇描绘,就被古希腊修辞学家称为“艺格敷词”(ekphrasis),一种“对一幅艺术作品的修辞学描述”。里奥·斯彼泽(Leo·Spitzer)称艺格敷词是“绘画或雕塑作品的诗意化描述”。由上可知,艺格敷词是指通过语言描述,从而再现某种造型的修辞手法,该修辞的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图像再现的虚拟效果。所以,尽管艺格敷词几乎已经被默认为一种典型的图像修辞,但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图像的“修辞”,其本质仍是摹仿理论基调下的语言修辞。
△《伊利亚特》
另一方面,由于“image”的多义性,“image”不仅可以指代真实的视觉形式,还可以意指精神图像(mentalpicture),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精神图像的再现也应被视为“图像修辞”。比如,米歇尔就从图像学视角,提出另一种意涵的“图像修辞”。他指出图像学中的“图像修辞”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关于“就形象之讨论”的研究,二是关于“形象之所说”的研究。米歇尔认为,前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斐洛斯特拉图家族《想象》(Images)系列的创作传统,“斐洛斯特拉图指出,他的兴趣在于绘画本身,而不是画家的生活,也不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历史关系。修辞学应该从绘画中汲取主题,因为希腊的绘画通常是从文学中汲取主题的”。可见,这里的“图像修辞”是指对绘画形象的描述或讨论,与前文所说的艺格敷词接近。而后者“形象之所说”则是指“形象自身通过劝说、讲故事或描述而言说自身的方式”,这种“图像修辞”主要探讨“诸如精神形象、词或文学形象以及人作为形象和形象创造者的概念相关方式”,即“图像修辞”亦可表示绘画如何以图像为媒介再现精神图像、叙述文学故事或者进行劝说。而这种“图像修辞”的研究,早已成为图像学、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迈克尔·安·霍利在《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一书中深刻指出该“图像修辞”的重要影响:研究者与艺术品的关系由“图像修辞的再现系统”所规定,绘画的修辞缔造诠释者的修辞策略。
《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
实际上,上述两种不同于巴尔特的“图像修辞”观点,都源自西方学者对摹仿论中再现观点的迷恋。艺格敷词旨在通过语言描述达致一种“如画”般的效果,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艺术则以图像再现圣经故事以宣扬理念。前者是以图像化为效果的一种语言修辞,而后者则通过摹仿语言文本的一种“图说”。总之,将图像视为“再现”和“摹仿”的观点造成了“图像修辞”和“图像再现”的混同。
“
三、“图像修辞”概念的生成逻辑
尽管摹仿论在西方十分盛行,但维特根斯坦对柏拉图的摹仿说和理念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图像和语言共存于逻辑空间内,图像并不是对现实的摹仿或再现,图像本身就是构成世界总体的组成部分。又由于世界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相同,而世界又是由图像构成的事实的总和,如此,语言才能够描述事实;而语言也亦如图像一样,语言与图像相互对应,并且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批判了西方长久以来的图像摹仿和再现理论,同时也将图像与语言放置在对等的位置上来讨论。不仅如此,纳尔逊·古德曼也质疑西方长期依赖的摹仿论,他直接指出:“任何程度的相似都不是再现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与再现不同,相似是对称的:B相似于A,就像A相似于B一样”。两个树相似但不能说其中一棵树再现了另一棵。至此,图像依据“相似性”再现客体的神话逐渐破碎。
维特根斯坦
纳尔逊·古德曼
但是,如果画家不依据相似性摹仿自然,又该如何进行创作呢?贡布里希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真之眼”,画家作画并非完全是“画其所见”。即使面对相同的景色,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画家所呈现出来的作品也会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艺术家跟作家一样,需要一套语汇才能动手从事现实的一个‘摹本’”。这套“语汇”就是画家所使用的“艺术的语言”,贡布里希将之命名为“图式”。图式是画家创作的起点,更是图像再现的基础。接着,贡布里希进一步指出再现和表现的辩证关系:画家要想塑造个人风格,彰显独具个性的图像修辞,关键在于突破图绘程式对绘画修辞的束缚,真正使绘画从再现自然走向艺术表现本身。当西方艺术家们意识到“图像再现”对艺术创新的阻碍后,他们开始摒弃相似性作为最高审美宗旨。从19世纪印象派的诞生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盛行,直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绘画的普及,可以窥见绘画摹仿论的式微。另一个角度,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已几乎达到“图像再现”的极致,这种“图像再现”即巴尔特所言的“无符码信息”的照片。上述种种迹象似乎都在催促着一种全新的“图像修辞”的诞生。
贡布里希
剔除图像再现对图像修辞的影响,意味着图像将现实再现与视觉设计分离开来。进而,无论是画家还是修辞学家都逐渐将重点转向图像的“修辞”。在这种背景下,罗兰·巴尔特通过吸收索绪尔等语言学家的理论,试图建立起一门包含图像修辞学在内的普通修辞学。其结果确实取得重大成效,同时也激发了学界对图像修辞学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然而,当我们回顾其研究的起点以及路径后就会发现,虽然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游刃于服装、照片、电影、音乐、书法等各类符号,但他始终以语言学理论作为一切修辞分析的注脚。也就是说,在巴尔特所构筑的符号帝国中,语言是全部符号的“提喻”,语言符号学是包括图像等其他一切符号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被德里达批判为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或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该观点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可见世界中的影像是无法抵达绝对真理的,只有“逻各斯本身凭借着辩证的力量”才能获得理性。换言之,语言代表着理性,决定着人类的认知与事物的真理。同样的,这种“语言论”潜意识也深刻影响了图像修辞的意涵以及图像修辞学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图像修辞的意指原理的揭示,还是图像修辞格的大量寻绎,图像修辞的这两种研究目标都旨在找到一套属于图像符号系统本身的修辞学,因而,图像修辞学的提出可视为是被笼罩在语言中心论潜意识中的图像研究的某种理论自觉。
如前所述,图像修辞学诞生于语言修辞学,但又意欲摆脱语言中心论的控制或影响,如此一来,语言与图像便处于一种相互扶持又相互对抗的张力之中。如果脱离图像修辞的研究视阈,纵观西方学术史会发现,语言与图像的竞争由来已久。《诗学》所谈到的各类摹仿艺术中,亚里士多德最倾向于悲剧,但是达·芬奇却认为绘画高于一切艺术。莱辛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艺术摹仿差别论,通过对比诗画得出“文学的天地比造型艺术的天地远较广阔”的结论。米歇尔·福柯通过马格里特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形象的背叛》两幅画中语词与形象关系的诘问,揭示出语言与图像在命名和指意上的矛盾。直至当今学术界,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仍是热点话题。总之,将语言与图像放置在一个对立面上探讨似乎是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前提。
△《形象的背叛》
并且,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图像被认为始终与真实相互对立,而代表逻各斯的语言却象征着绝对真理。于是,“图像修辞”自身便成为了一个悖论,因为无论是混淆“图像再现”和“图像修辞”观点,还是图像的“修辞”的符号学分析,图像都离不开语言的描述。也就是说,“图像修辞”概念就是在形象与语词的辩证关系中生成的。
事实上,这种隐藏在“图像修辞”概念中辩证法,并非始于巴尔特的“独创”,而是在西方思想史中“蓄谋已久”。尽管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时刻警惕着图像对绝对真理的侵蚀,但其实柏拉图本人并未将图像全部驱逐出他的哲学王国,他论述中如床喻、线段喻、洞穴喻等高度形象化的语言便是最好的证明。美学家安东尼·卡斯卡蒂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柏拉图的图像观颇有误解,柏拉图并非拒绝所有的图像,而是对图像的真伪有所判断,“在柏拉图那里,只要图像真正地指涉永恒的理式,就能得到认可”。
总而言之,巴尔特提出“图像修辞学”,既有时代因素,又有哲学根源。而“图像修辞”概念之所以内涵混乱、含义交叉,根本上是因为形象与语言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萌芽,自古希腊时期就潜伏在哲学、诗学之中。然而这种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副作用,它催发了西方长久以来诗画对立的观点,同时也使得语言和绘画常常处于一强一弱的状态。于是该思想直接造成了摹仿论大前提下,人们将“图像”与“图像再现”混淆,还将“图像”与“现实相似”等同起来。而到了现代社会,“图像修辞学”之所以能够独立为一门科学,其中暗含着的是人类对世界认知和认知方式的变化逻辑,以及现代美学研究中去中心化思潮所带来的范式重构。说到底,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再到米歇尔的图像理论,其中始终隐藏着语言与形象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