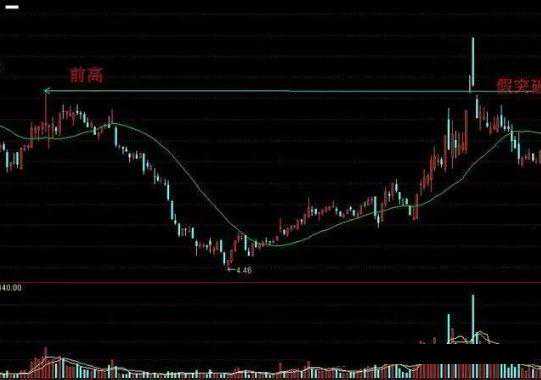王泽民同志从一九六四年积累资料起,历时十九年,几经周折,至一九八二年五月,搜集编纂了一部《北路梆子音乐》,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山西有北路、中路、上党、蒲州四大梆子,它们同陕西的同州梆子、秦腔,以及其它省区的梆子、乱弹戏一样,都是由山、陕、豫三角地带的“山陕梆子”先后演变分化而来。北路梆子只是梆子戏大家族中的一个支派,它在梆子声腔剧种中却占有重要地位。
正因为梆子乱弹这一新兴戏曲艺术吸引了广大观众,因此,连当时的雅部演员如吴大宝、时瑶卿、张发官、郑载兴等人,也都学起梆子乱弹来了。保和部本来是个雅部班子,为了争取观众,不得不杂演乱弹和武戏,此后的保和部竟又分化为文武两部。《燕兰小谱》所“列诸伶以甲午为限”,甲午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述事实,说明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花部努力的影响,更说明了梆子乱弹这一“两句式”曲体结构为基础的戏曲声腔艺术生气勃勃的艺术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的“山陕梆子”在晋中、晋北成立班社,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教戏必须请蒲州或同州老师。成立科班,以招收蒲州、同州娃娃为上策。舞台上必须念“蒲白”,唱“蒲腔”,以保持与梆子戏发源地艺术风格的统一。
武承仁同志在五台县槐荫村西戏台木板隔断上照录的“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吉日,山西省太原府代州五台县东寨村自成班”一台戏的演出题壁,据我分析,实际还属于“山陕梆子”在各地成班时期的演出。这一时期的所谓山陕梆子、山西梆子、秦腔等叫法不同,其实还是一个剧种的几种称呼。在剧目与演法上初步有些地区性流派的区别,由于念白、唱腔强调了蒲州、同州这一三角地带语音等艺术规范,其流派区别并不大,相互串演倒是很方便的。八十年前的晚清时期,“山陕梆子”盛极一时,脚迹遍及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东北越过哈尔滨,直至伯力,南达上海,都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北京有五大戏园,前门外的“华乐”、“广和”、“中和”、“三庆”,都是梆子戏的主要活动场所,只有城里的“吉祥”才是京戏的牢固阵地。京戏科班培养人才,直到富连成科班梅兰芳这一班的训练,也还是由梆子戏老师与京剧老师合教的。晚清梆子戏极盛时期,直到民初,曾出现过一大批负有盛名的优秀演员,如侯俊山(十三旦)、郭宝臣(元儿红)、油糕旦(西来凤)、留留旦、史灵芝、毛毛旦,以及十三旦的徒弟、梆子戏的第一位女演员刘喜奎,更是青出于蓝。谭鑫培是当时京剧名宿,但是,只要刘喜奎一挂牌,谭鑫培就不出戏了。有时梅兰芳、谭鑫培、刘喜奎同台演出,刘喜奎即唱压轴戏。这些都标志着梆子戏的黄金时代。这里说几句识别梆子戏剧种分化的小小插曲,即以名伶十三旦(侯俊山)为例。有人说他出生于晋南洪洞县周壁村,就说他是蒲剧演员;也有人说他九岁入太原某科班学艺,工梆子戏花旦,就认为他是山西中路梆子演员;也有人强调他一个时期在晋北农村和张家口一带演出,甚至垛箱后,回晋北教过戏,即认为他是山西北路梆子演员;还有人认为他起初在张家口演出,成名后常在北京附近活动,晚年又定居张垣,即又认为他是河北梆子演员;还有人说河北梆子解放前一直号称秦腔,所以认为他还可能是秦腔演员。这似乎有点像希腊史诗歌唱家荷马的传说。荷马晚年在雅典等八个大城市轮流演出,难以糊口,死后由于出版了他演唱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名著,使他芳名远扬。于是,八个大城市都争说他是荷马的故乡。其实这一时期的“山陕梆子”,即使在山西境内,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清二楚的四大梆子剧种,包括变化较早较大的上党诸宫调,基本上都还是山陕梆子的晚期。维克多唱片公司这一时期灌片,仍称它是“山陕梆子”。十三旦所以能在各地串演,正说明了山陕梆子尚未彻底大分化的特点,何况其中如说十三旦的出生地问题,也还是有异议的。
梆子戏并非按照明清时期的行政管辖区划产生,而是由两句式声腔结构的劝善书、说唱音乐、傀儡戏,结合山陕豫三角地带方言语音的“音色片”关系形成。当它班社日增,流布范围扩大之后,也会按照新活动地区的“音色片”地区所同化。原山西晋南和陕西关中地区及河南陕州、灵宝一带,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共同隶属关系和地理、交通上的种种便利条件,使这一大片的方言语音、民俗风情、群众生活习惯,形成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特点,所以才能在这一地区人民群众中形成一种共同喜闻乐见而又新颖别致的两句式“山陕土戏”和“梆子戏”。最初,这种梆子戏的定名,并未冠以行政区划的名号,它是这一片地区劳动群众自己欣赏的民间戏曲艺术,它在上层社会眼里地位不高,所以起初才有“土戏不能敬神”之类说法。
戏剧艺术的魔力是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转移的,观众如果欢迎它,班社就要增长,跑江湖走远了,各地出去的班社才按班主的地域冠以地区性的名称,如同州梆子、蒲州梆子,实际隔河相望,仍是一种形式,甚至从业人员也是两地插花入班的。任何声腔艺术,当它离开产生它的土壤,长期流传到外地之后,也总不免要受到新的“音色片”地区的同化或异变,这是“音色片”规律制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武安落子流传到上党地区扎根开花,就按照上党地区人民群众的要求,逐渐变成了上党落子;皮黄传到了四川,也就变成了赋有四川特色的“胡琴腔”。“山陕梆子”传遍了山西,而晋中、上党、晋北地区的方言语音、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特色与群众欣赏习惯所形成的音色片特点,不只都与晋南不同,而且相互各异。因此,“山陕梆子”在这几处音色片地区逐步地被同化,开始形成了上路调、中路调、下路调(或南路调、西府戏)和上党、泽州调等地区性流派。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打破了封建王朝长时期对民间戏曲的种种禁令,资产阶级改良之风日盛,各种封建行帮习惯的破产,也影响到蒲州、同州一带艺人统治梆子戏舞台的统治行业习惯的改变,而由各个“音色片”地区土生土长的演员所代替,虽然也还讲究念蒲白,唱蒲调,在声腔艺术方面,实际都在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音色片”地区的特点加以融化或同化,也可以说是各个地区都在自发的对梆子声腔进行改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波及戏曲界,二十年代起,梆子戏舞台上也出现了“文明戏”(即时装戏)。坤伶登台献演,逐年增多,男女同台演出,也促进了地区性流派不平衡的急剧分化,使它们很快地转化为英姿独立的几种梆子戏。北路梆子也是从这条道路上演变过来的。作为上路调流派存在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它在群众中由上路调真正命名为北路梆子,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前后的事。由山陕梆子的上路调演变而形成的北路梆子声腔艺术,在花腔发展与曲牌使用上,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胡琴适应了它的调高,也与中路、蒲剧不同。当它的音乐个性确立之后,同时也就和它的音色片范围结了血缘关系。“音色片”又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上路调或北路梆子,最早活跃于忻县、阳曲之间的石岭关以北,直至内蒙的呼市、包头。偶尔也去东口的张垣,但不是它的主要流布范围。这一声腔艺术,既有梆子戏的共性,有自己的个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近四、五十年来又形成了大北路、小北路两大流派。这里所谓大小北路,据了解并无褒贬之意,所谓“大北”,是指“最北面”的意思,“小北”是指“近北”。雁门关以北直至内蒙,以王玉山(水上漂)为代表的大北路声腔,其特点以行腔稳健深沉见长;雁门关以南,以贾桂林(小电灯)为代表的小北路声腔,以行腔活泼华丽、委婉柔媚见长,两大流派确实各有千秋。此外,河北蔚州也算一个流派,在戏路上有些差别,声腔上实际尚未形成独特风格。
王泽民同志搜集记录和编纂的北路梆子音乐,以大小北路唱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宗旨,同时也还将忻定鼓吹乐名师胡金泉等同志别具一格的北路梆子吹奏乐,亦包括在内。全书共分六章,五十个小节,其中仅文场曲牌一项,共收集丝弦曲牌七类,一百六十三支;唢呐曲牌十二类,一百五十二支,合计曲牌竞达三百余支之多。各流派各个行当唱例选段和完整的唱腔选段,包括王玉山、贾桂林、高玉贵、孔丽珍、两股风(佚名)、周成贵、宋玉芬、刘明山、李定官、郭占鳌、安秉琪、刘正芳、达达旦(佚名)等可以收集到的著名演员唱腔和胡金泉戏剧吹奏,合计二十段。全书将近三十万言,虽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也确实是一部抢救和记录北路梆子音乐的重要图书了。此书出版,可能还要费些周折,我则以本书的初稿内部印刷感动欣慰,也为王泽民同志的艺术劳动表示敬意,因为他对北路梆子声腔艺术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富的音乐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