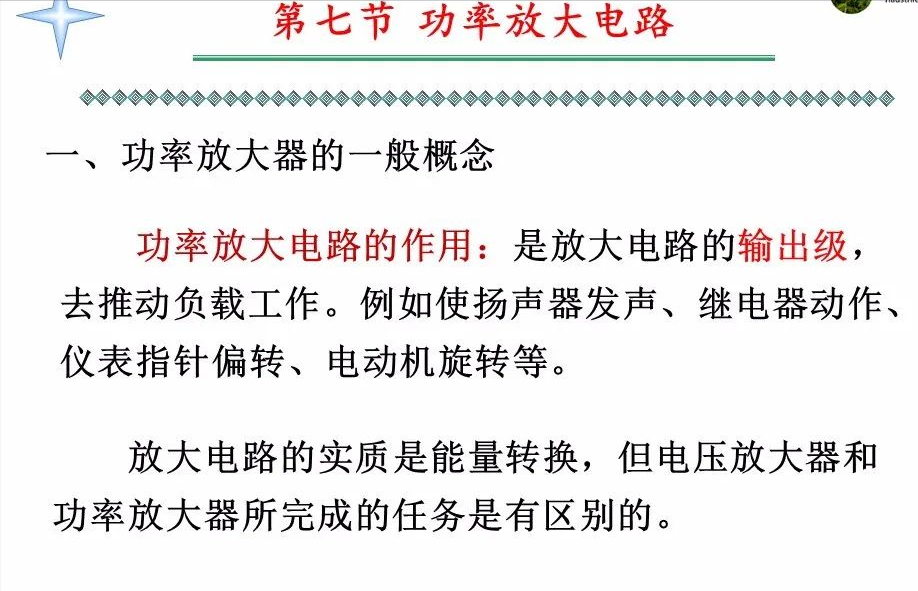一九七九年,生产队解散分家;秋收后,分田分畜分农具到户,农民开始单干。由于耕地头口(驴骡牛等牲畜)偏少,生产队订的规定是:如果想要驴,可以一家分得一头;如果是骡子或牛,只能两户人家合分得一头。为此,我家和邻居家合分得了一头两岁牙的红骡子。后来缘于两家合使一头头口的诸多不便,两家商量将红骡作价,要骡的一方付给另一方骡价的一半钱。可两家都想要骡子,父亲极喜红螺,所以忍痛多给了邻家五十块钱,争得了红骡。那年头一个建筑工匠日工资三角五分,五十块钱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钱。
红螺身高腰壮、体长腿健,长大的两只耳朵硬竖,铜铃般一对枣红大眼睛,额上两眉间偏上有拳头般大的一圈黑毛圆坨,鬃毛粗硬遒劲齐整,浑身圆实壮健,像裹着一层绛红的缎面,锃光闪亮。它的父亲是原生产队的一头黑驴,母亲是一头红马。骡子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它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公为驴、母为马交配产的叫马骡,个头比马都大;公为马、母为驴交配产的叫驴骡,个头稍小。也基于此,骡子性格中既有马的忠诚与灵性,也有驴的犟拗与顽劣。
奇怪的是,骡子虽有公母之分,但由于某种生理缺陷,几乎没有繁殖能力。因此农谚说,一头骡子一世界,不问祖联没后系。骡驹子一般从生下长到对牙(一年半)以后,就开始调教耕地拉田,劳累一生终其到老,注定是悲惨的。也所以在一些农村地区,人骂人极重时,咒对方下世为骡。
红骡在生产队里没有使唤过,到我家的翻年春种,是对它的调口期:学牵犁耕地,学套辔拉车,适应骑人驮物……整整一年,犁地也好,拉车也好,都要人在笼头上牵它才能步入正规,合乎境地。那一年,父亲使唤它时,总是由我经常牵它,脚后跟和鞋不知被它踩烂和踏破了多少次,气得我经常牙痒痒。如今,我的脚后跟上还留着当年套犁田埂地边时牵红骡尽力靠埂靠边而被它踩伤的印记。
红骡身健劲多,但也特别顽皮,也非常犟拗,一般人也使唤驾驭不住。拉犁耕地到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它就开始尥蹶子,如果父亲执意不解辔卸犁,它会在地头转弯时强行拖犁冲出地块往家中跑。父亲曾经诧异于它对时间的准确感知,春夏秋冬日头是不一样的,还有天阴下雨,就是人类若不看表,也无法精确肯定时间,但红骡总是准时在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罢工”。
骡子相较于牛,劲力相当。牛性慢,喜用柔劲,载田套粪,不慌不忙慢悠悠地就爬上了坡。而骡性快,善用猛力,拉车上坡,是靠猛力冲一半爬一半。有些骡子拉重车上陡坡,遇车太重爬不上去的情况,甚至会出现骡子侧身脱辔停拉罢牵的现象,极其危险。红骡遇到车太重坡太陡的情况,干脆在坡底是不上路的,气得父亲有时狠狠地拿鞭子抽它,但它就是不为所动,越打越毛,立场越发坚定。每次父亲打完它,它总是把头扬得高高的,然后猛地低头打个鼻响,同时把一只前蹄狠跺一下,一副不服输不服气的架势。久了,知它脾性了,只好顺着它来。犁地的一天,中午一点以前解辔脱犁,如果是拉粪拉田,路途有极陡的坡,就提前把车装轻点。
民间谚语“哄骡顺驴”,就是这么个道理。
头口犁地,一般都是驾一对驴或一对骡牛才能拉得动犁,除非劲力特别好的骡或牛,驾一头就能单扯(指一头牲畜拉犁耕地)。红骡力大,在我家前十年一直是单扯犁田磨地,省去很多草料不说,也减轻了照料头口的很多功夫与精力。
我小的时候,周末或是节日放假,主要任务是经管红骡。中午傍晚都要按时牵它去村中沟里饮水。那时老家农村靠天吃水,在庄外地势低处挖水窖储积下雨下雪天屋面和院内的雨水和雪水用以吃用。十年九旱,窖里的水人吃饮用都紧张,所以牲畜饮用水就去村里深沟中一眼泉水处,那水又咸又苦,盐碱特重,但牲畜却极爱饮用,而且饮那泉水的牲畜毛皮展亮,身壮力健。每天下午或是不耕地拉田使唤红螺的全天,我的任务是牵它去黄坡野地或收过庄稼的地里放牧它。红螺刁顽且贼灵,女人小孩使它,它便欺你力薄,稍不留神,有时甚至强行从我手中挣脱缰绳撒欢而奔,也不知它要奔向那里去,更不知它为何要狂奔起来,只是高扬头颅,硬竖红鬃,奔步如飞,一路疾驰,呱嗒呱嗒四个蹄子翻飞如浪,害得我追它挣得肠疼肺痛,上气不接下气。跑一阵它就会停下来低头佯装翕动唇齿啃啮路边的野草,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瞟到我快靠近它了,又仰头硬脖狂奔而去……反反复复,直至它尽兴后,就会在某个坡地啃草撕皮,待我牵它。我气得真想狠狠暴揍它一顿,无奈它又高又大,又怕它受惊再跑,一时无可奈何。有时疯跑乱穿会践踏到别人家田边地头的庄稼,引得村人嗔骂怨怪。父亲知道后也总是装如未闻。父亲是极呵护红骡的,没事的时候总把骡身杂毛污片刮刷得干干净净,骡圈也打扫得干燥清洁。遇使重力的几天给红骡加豆加料,冬天怕它挨冻受冷,在圈窑张挂加厚门帘,在红骡背上绑覆薄被。也许是基于此,红骡对父亲也是唯命是听,言从斥受的。